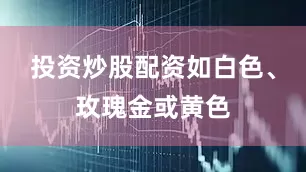咱们今天聊聊一本挺特别的书,叫《南山谷口考》,作者是清代的毛凤枝。
这书专门讲陕西秦岭北边的河谷,还有关中地区的安危,是本军事历史地理书。
从它出来到现在,因为时代背景特殊,学术价值也高,在历史地理圈里一直挺有分量。
不过呢,这书流传的时候,有个名字被搞错了,让后人有点糊涂——那个常被提到的刻书人郑子平,到底是谁?后来一点点查史料,真相慢慢清楚了,原来那个刻书人其实是个叫郑维翰的长安文人,字子屏,被历史的灰尘盖住了。

一、一本能决定关中能不能守得住的地理书
要理解《南山谷口考》多重要,得先知道秦岭北麓那些河谷有多关键。
秦岭横在陕西南边,它北边的河谷,像子午谷、褒斜谷、陈仓道这些,不光是连接关中跟四川的路,更是保护长安的天然屏障。
毛凤枝在书里把谷口当重点,一条一条考证从周朝到清朝的河谷走向、关隘怎么建的、哪些战役在这儿发生,还有它们在打仗时的战略作用。
他在书前面的序里直接说:南山谷口就是关中的大门。你想啊,汉高祖在关中定都,韩信明修栈道,暗度陈仓,就是从这儿打的仗;唐朝天宝年间安禄山叛乱,哥舒翰守潼关,也是靠着这些谷口的险要。
毛凤枝当时是西安府的清军同知,他的考证不是瞎写的。
他自己也常去秦岭北麓跑,把以前的地方志和自己实地看的结合起来,纠正了不少以前书里写错的地方。
比如他就指出《水经注》里把斜谷的走向搞错了,后来通过研究石门栈道的遗迹怎么分布,重新理出了褒斜道真正的路线。
这种把书上学问和实地考察结合的研究方法,让他的书又严谨又实用,所以民国时候的军事专家都把它当成带兵打仗的人必须看的书。
二、郑子平和郑子屏,名字怎么就混了?
《南山谷口考》怎么流传下来的,有个关键细节在《关中丛书》版本的跋里。
编《关中丛书》的宋联奎在跋里写:近代的郑子平曾经刻了二百部,带兵的人觉得对打仗有用,分着拿光了,市面上买不到,所以流传不广。这段记载让后人以为郑子平是最早刻这本书的人,但郑子平这个名字,在其他书里都找不到,连学者李之勤都叹他的事没人知道。

王民权先生研究的时候发现不对劲:子平和子屏读音差不多,屏字在清朝文人里又挺常见,会不会是子屏写错了?他带着这个疑问,去翻长安的地方志和文人的碑刻,最后在《宋芝田先生文集》里找到个关键东西——宋伯鲁写的《郑子屏墓志铭》。
这个和郑子屏关系好的清朝大学者,在文章里写:庚午年(1930年)春天,长安的郑子屏,名字叫维翰,他弟弟叫维藩,从南海回来,在志局见了我。这不就清楚了嘛,郑子屏就是郑维翰,字子屏,子平肯定是子屏写错了。
三、从留日学生到刻书人的郑维翰
郑维翰(1886-1927)的经历,比我们想的还传奇。
《郑氏族谱》和宋伯鲁的《墓志铭》里说,他是长安书香门第的孩子,从小聪明,1913年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,专门学军事地理。
回国后,他又考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接着学,毕业之后就去了军队,当过陆军第一骑兵旅的参谋、督署参军这些官。
那时候军阀老打仗,他看到外国欺负我们,国内又乱,总觉得带兵得懂地理有多重要,正好毛凤枝的《南山谷口考》就是本难得的军事地理教材。
1926年,军阀刘镇华打西安,郑维翰当时是督署参谋,也参与了守城。
就是这段经历,让他特别明白地理在打仗守城里有多重要。
他在日记里写:要是不知道谷口的险,怎么守关?要是不懂河谷的重要,怎么打败敌人?所以他就托关系,找朋友把《南山谷口考》用木版刻出来,印了二百部,送给军队里的同事和地方官。
这二百部书没流到老百姓手里,但在西北军界影响特别大。
后来《陕西军事志》里写,1930年冯玉祥布防潼关的时候,他手下的将领还在看郑维翰翻印的这个版本。

四、被重新发现的历史价值
郑维翰刻书这事儿,不光让《南山谷口考》能继续传下去,它的学术价值也慢慢被后人看到了。
20世纪50年代,历史学家史念海研究秦岭古道的时候,专门参考了《南山谷口考》里对褒斜道的考证;80年代的时候,陕西地方志办公室整理《关中丛书》,也是用郑维翰最早刻的版本来校对。
这些都说明王民权先生考证得对,那个被错写成郑子平的文人,其实是个有军事本事又懂学问的长安好人。
现在在西安长安区杜曲镇的郑维翰墓前,还能看到民国十六年(1927年)四月七日的碑,这个死得早的军人兼文人,可能自己都没想到,当年一个顺手的事,让一部地理学名著能接着传下去。
《南山谷口考》的流传故事,也成了整理历史文献时辨真假的例子——要是在资料里看到不清楚的名字和记载,只有仔细考证,才能把历史的灰尘扫掉,让那些被忘了的人和事重新被知道。
从一本地理书到能让人想很多道理,《南山谷口考》的版本故事,不光是书怎么传下来的,也是一个被写错名字的长安文人的人生故事。
我们再看这本书的时候,可能会想起那个在打仗的年代,为了保护家国安危而看古书的人,他的名字,本来就该被记住。
配资客户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